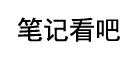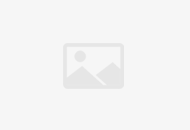一、破题:当围棋哲学遭遇生存困局
1.1 棋盘内外的生存隐喻
《棋士》以围棋为叙事核心,构建了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道德寓言。剧中崔业(王宝强饰)的堕落轨迹,恰似一盘被现实篡改的棋局:本应在纹枰之上运筹帷幄的棋士,却将“气”“劫”“眼”等围棋要义异化为犯罪密码。当他在信用社劫案中,用“弃子争先”战术帮助劫匪突破警方封锁时,围棋的哲学维度轰然崩塌——这种技艺不再是“手谈”的雅趣,而沦为生存博弈的暴力工具。
编剧巧妙运用围棋术语解构犯罪心理:
“逢危须弃”:崔业为筹措儿子医药费,主动放弃职业棋手尊严向富商输棋,暗示其道德底线的首次松动;
“打劫循环”:每次犯罪后看似成功的逃脱,实则是更深重危机的开端,如同围棋中永无止境的劫争;
“金角银边”:他将城市地形图视作棋盘,利用边角建筑构造逃生路线,这种空间智慧的反向运用令人脊背发凉。
剧中反复出现的围棋残局(如“珍珑棋局”),成为人物命运的镜像:崔业在现实困境中左冲右突,却始终找不到破局的“真眼”。这种将传统文化符号解构重组的手法,让观众在熟悉的意象中感受到陌生化的惊悚。
1.2 知识分子的精神坍缩
崔业的身份设定极具现实痛感:少年宫围棋教师、业余比赛冠军、寒门知识分子的三重标签,构成当代社会“高知底层”的典型样本。他的堕落并非传统反派式的欲望膨胀,而是尊严被系统性碾碎后的绝望反击。
三次尊严剥夺的递进式刻画:
物质羞辱:少年宫克扣奖金,用复制品奖杯打发冠军,暗示知识价值在资本面前的贬值;
精神践踏:富商要求其故意输棋时轻蔑的“这是你十个月的工资”,将智力博弈异化为金钱交易;
伦理崩塌:发现妻子成为商人秘书时的沉默对视,击碎其作为丈夫的最后体面。
这些细节共同编织成一张“平庸之恶”的网:没有脸谱化的恶人,但每个环节的微小恶意叠加,最终将人推入深渊。这种叙事策略,让观众在愤怒之余更感窒息——我们是否都曾是这张网上的丝线?
二、叙事解构:日常细节堆砌的犯罪史诗
2.1 生活流叙事中的暴力美学
导演摒弃传统罪案剧的强情节轰炸,转而采用“温水煮蛙”式的日常化叙事。全剧没有炫目的枪战场面,却在以下细节中暗藏惊心动魄的张力:
符号暴力:崔业常年穿着的灰色夹克与兄长笔挺警服的对比,母亲扫墓时对长子奖章的反复擦拭,这些静默的镜头语言构成身份压迫的具象化表达;
空间政治:信用社专用停车位、少年宫破败的棋室、城中村逼仄的出租屋,不同空间构成阶层分化的地理注脚;
物品隐喻:反复出现的白糖(象征底层对甜蜜生活的卑微渴望)、鱼缸中的死金鱼(暗示道德生命力的消亡)、被踩碎的眼镜(知识分子尊严的粉碎)等意象,织就一张精密的隐喻之网。
2.2 时间迷宫的叙事实验
剧集打破线性叙事,通过三条时间线的交错并置,构建出命运轮回的宿命感:
1998年:少年崔业在围棋赛中击败兄长,却因家庭贫困放弃职业道路;
2003年:信用社劫案成为人生转折点;
2022年:已成为通缉犯的崔业匿名资助贫困棋手,完成罪与罚的闭环。
这种结构让人联想到《百年孤独》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:过去的选择如同幽灵般缠绕当下,而现在的每一个决定都在重写历史。当老年崔业在监狱中与年轻时的自己对弈时,棋盘上的黑白子仿佛凝结了二十年的人性挣扎。
三、人物光谱:灰度地带的灵魂解剖
3.1 崔业:堕入深渊的普罗米修斯
王宝强贡献了职业生涯最具突破性的表演:佝偻的脊背、神经质的嘴角抽动、永远低垂的视线,将人物内心的压抑与扭曲外化为肢体语言。三个经典场景展现其精神裂变:
雨中弃棋(第4集):在瓢泼大雨中撕毁获奖证书,却小心折叠好儿子的医药费收据,展现父爱与尊严的惨烈对冲;
镜前独白(第12集):对着破碎的镜子练习微笑,试图模仿“正常人”的表情管理,揭示其身份认同的彻底崩解;
终极对弈(大结局):与兄长在审讯室用饼干当棋子对局,落子时颤抖的手指与突然爆发的狂笑,完成自我审判的仪式。
3.2 崔伟:正义面具下的阴影
陈明昊饰演的刑警队长打破“伟光正”套路。三个细节暴露其人性裂隙:
秘密档案:私自保留弟弟幼年棋谱,暗示其对崔业天赋的嫉妒与愧疚;
暴力审讯(第15集):对嫌犯的过激刑讯,暴露其以正义之名的权力偏执;
临终遗言(第22集):弥留之际喃喃“当年该让你去北京学棋”,完成加害者的自我忏悔。
这对兄弟如同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:崔业用犯罪对抗命运,崔伟用法律维护秩序,但他们都困在各自偏执的“气”中无法和解。这种设定跳出了简单的善恶二分法,直指人性本质的混沌。
四、社会切片:转型中国的疼痛标本
4.1 资源错配下的集体焦虑
剧集以世纪初南方城市为缩影,解剖社会转型期的阵痛:
教育产业化:少年宫将围棋班改为英语培训班,折射素质教育向功利教育的妥协;
医疗市场化:崔业儿子因费用中断治疗,与VIP病房富商孙子的对比,展现医疗资源分配的残酷落差;
权力市场化:商人通过赞助比赛操纵赛果,暴露公共领域被资本侵蚀的现实。
4.2 底层互害的生存逻辑
剧中呈现的“恶”具有鲜明的时代胎记:
假奖杯产业链:下岗工人老周为谋生参与制作仿制奖杯,成为羞辱崔业的帮凶;
黑车司机告密:为五百元举报崔业行踪,展现贫困群体间的信任瓦解;
医药代表回扣:医生对高价药的推销,完成对患者的二次剥削。
这些情节构成一幅“饥饿游戏”式的生存图景:当整个社会陷入零和博弈,道德便成为最先被舍弃的奢侈品。
五、艺术突破:类型剧的本土化重构
5.1 罪案剧的东方美学转型
《棋士》在三个方面实现类型突破:
思维战替代动作战:警匪较量从枪械对抗升级为围棋思维的降维打击,如崔业利用“征子”原理预判警方布控;
文戏武拍:关键冲突场景(如兄弟对峙、夫妻摊牌)采用围棋术语替代直白台词,形成独特的戏剧张力;
留白艺术:大量使用空镜头(如雨夜棋院、晨雾江面)营造古典意境,让暴力叙事获得诗意缓冲。
5.2 音乐与画面的复调叙事
作曲家董冬冬以古琴泛音模拟落子声,用电子音效制造心理压迫感。第18集追捕戏中,三弦急促的扫弦与监控画面的跳切剪辑,构建出令人窒息的节奏迷宫。这种声音实验,让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叙事中焕发新生。
六、争议与反思:在赞美与质疑之间
6.1 艺术真实性的边界探讨
部分观众质疑:围棋战术能否真实应用于犯罪?对此需厘清两点:
戏剧合理:剧中犯罪手法(如利用围棋“气”的概念设计逃生路线)虽经艺术夸张,但其内在逻辑符合“思维移植”的创作规律;
象征优先:围棋在此更多作为人性异化的隐喻载体,而非犯罪教科书。
6.2 与《绝命毒师》的对话关系
尽管被称作“中国版白老师”,但崔业的堕落更具本土特质:
动机差异:老白为自我实现犯罪,崔业为家庭责任越界;
救赎路径:沃尔特通过制毒获得存在感,崔业却在犯罪中加速自我毁灭;
文化基因:前者体现个人主义困境,后者折射集体主义重压下的个体崩解。
七、结语:在满盘皆输中寻找活着的坐标
当崔业在最终对弈中主动投子认负,这个动作既是对犯罪的忏悔,也是对命运的终极反抗。剧集留给观众的,不是简单的善恶评判,而是一面照见时代病症的镜子。在这个“人人皆在局中”的世界,或许真正的破局之道,不在于如何赢得棋局,而在于能否在落子前听见良心的震颤。
《棋士》的价值,正在于它撕开了温情脉脉的生活表象,让我们不得不直面那个永恒的诘问:当生存与尊严成为非此即彼的选择题,人性究竟能在黑暗中坚持多久?这个问题的答案,或许就藏在每一颗棋子与现实的碰撞声中。